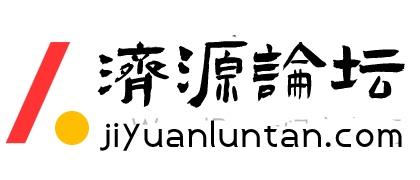1.关于余秋雨《山居笔记》的好句好段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2.山居岁月第一章好词好句,,,
前几天妈妈给我买了本国际大奖小说《山居岁月》,主人翁山姆是个纽约男孩,在五月的一天离开家,带上他早已准备好的一把小刀、一捆绳索、一把斧头、一些打火石和钢片,去克斯奇山,寻找曾祖父遗留下来的葛博礼农场的故事。
他在一座大森林中,自己烧树洞做房子,为自己做了一个大树屋,他为了谋生,自己四处捕猎寻找食物,历尽艰险做陷阱,凭着他的机智、勇敢把一只刚出生的小鹰训练成猎鹰,还用火把一棵铁杉树烧成了空心书屋,年仅10岁的他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家,过着无忧无虑,幸福的生活。
书中山姆面对大自然的挑战临危不惧,他的机智、勇敢、独立、坚定、坚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最使我感兴趣的是第十五章“打猎”,讲的是在打猎季节,山姆潜伏在树上,窥视猎人打猎,当猎人打中猎物而找不到而着急时,他就把他训练的猎鹰惊风放出去,利用它把猎人引开,趁机下树,获取猎人找不到的猎物,我佩服山姆的独立性,更佩服他的胆量、勇气和信心。
这本书很好,特别值得我们同学读一读,书中的好词好句都用的十分恰当,而且每一章节都充满了幽默性。如果你还没读过这本书的话,我奉劝你赶快买来读一读,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3.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中的好词好句级对句子的短评
这些日子突然莫名其妙地觉得心浮气躁,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度过的。百无聊赖之际便随手翻阅了书桌上一本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姑且不说是想从书中寻找些许心灵上的慰藉,但至少可以当作是来消遣无聊的一种方式吧!
我想我一直以来都不是那种善于读书的人吧,总觉得自己既缺乏潜心鉴赏的定性,又没有那种体味美感的修为。想想以前看书,多半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般的一览而过,久而久之便留下了近乎囫囵吞枣式的劣根性—枣自然是被吞下肚了,口中却依旧索然无味。因此,每次要写诸如读后感之类的文字时,便难免有些捉襟见肘的窘迫感。
但这次看完《山居笔记》之后,倒是自认为感觉有些奇怪,因为我竟然从那些挥洒自如的文字中嗅到了些许的味道。确切地说应该是透过字里行间,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上的碰撞,或许这就是通常说的所谓心灵上的共鸣吧!
应该说全书没有诗歌那样唯美华丽的辞藻,也少了杂文那般犀利精辟的笔锋,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摈弃了浮华的随性,给了人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感—自然流露出来的文字往往能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作为自述性笔记,初读起来似乎有些凌乱琐碎,但通读全书,却不难发现作者构思之精妙:那就是从平淡的话题中以小见大,通过质朴的语言风格直指社会现实,从而使得文章中所触及到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现实遥相呼应—轻快中不乏沉重,从容中又不失理性的批判。由此把一个社会现实的剖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形中引发并启迪人们的深思,从而点明了人类应该回归自然、崇尚清雅淡泊的主题。
可能我对这些文字的理解很肤浅,而对作者文学心理的解读也只是停留在很浅薄的层面上,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自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吧。的确,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我们多数人都热衷于名与利的追逐,醉心于粗浅的感官上的享受,却忽略了太多原本值得自己去关注去体味的东西。我们每天麻木地跟着紧张的社会节奏而躁动,却在躁动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失去了自我,我们守住了眼前那些自以为珍贵的美丽,却始终守不住一颗淡泊的心,直到有一天看到那个面目全非的自己,才猛然感觉到了疲惫……
还是看看作者在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所持的心态吧—即使喧嚣声中夹杂进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也只在远处飘忽,烟雨渺渺。
或许从中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丝的宁静。当铅华褪尽,我们带着苍茫的心态回首走过的路,能够很坦然地微笑着告诉自己—我曾经也是那么充实过的!这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心灵一个最完满的交代。
4.求余秋雨的< >的好段摘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
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
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
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
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
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谕,废除科举。
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
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
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
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
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
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
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
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
5.山居岁月的好词好句
作者简介:珍.克雷赫德.乔治是一位热爱大自然、以写作自然故事为主的美国著名儿童文学家。
《山居岁月》的故事就是她童年的梦想,而故事中山姆的野外求生技能,主要来自她童年的生活经验。好词好句:口干舌燥 活蹦乱跳 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饥寒交迫 可怜兮兮 高谈阔论 夏去秋来,冬去春来。
在四季的更迭和万物的变迁中,山姆学会了谛听和凝视自然。夜莺的扑翅、猫头鹰飞跃大地时的啸声、徘徊的鹿群、被冰雪冻裂地枫树、、、、、、这些都不仅仅是动听的声响和美丽的景色,它们更是克斯奇山这一片荒野有致的呼吸与节奏。
最喜欢的片段:现在到处是鸟儿鸣唱的和声,树木披上夏季的绿衣,六月的气息满山谷。空气闻起来清香,食物吃起来甜美,放眼尽是绿意怏然、、、、、、明白的道理:做事要有安排,面对困难要沉着冷静、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