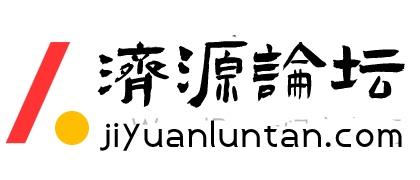1.我想看陈布雷的文章,谁能帮我找几篇
陈布雷当了总统府国策顾问,还是给蒋介石在政治上、文字上出谋、执笔,一直到死去。
陈布雷曾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给蒋介石当上幕僚长的契机,自谓“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1927年2月初,阴历除夕夜,陈布雷与潘公展到了南昌。
第二天,两人一同去见了蒋介石。陈布雷很恭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
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蒋介石对陈布雷确实也很尊敬,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
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此后每隔几天,蒋介石必召陈布雷谈话。
有一次,他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十分烦躁,张静江见状问道:“介石,你有什么心事?” “想发表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告黄埔同学书。”
蒋介石还是来回走着道:“北伐进展甚速,我黄埔学生战功卓著,但派系分歧,潜伏隐患,这篇文告要动之以情,要有文采……” “叫布雷试一试吧!” “好,好,”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就照我讲的意思写份《告黄埔同学书》,这篇文章要得很急。” 陈布雷就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研墨铺纸,挥笔而就。
陈布雷一边写,蒋介石一边看,连声称赞:“好!好!”他把文章交给副官说:“立刻去排印。”又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今后愿否在总部工作?” 陈布雷说:“蒋先生,我仍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
“唉!”蒋介石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好生奇怪:“这个书生不愿当官?” 编写《西安半月记》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南京没几天,准备到上海去治疗,他对陈布雷说:“你到上海贾尔业爱路住宅来看我吧!我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其间蒋介石曾去奉化溪口、杭州休养,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他叫陈布雷一直跟着他。
蒋介石因腰部受伤,多数日子卧在床上。他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给我撰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把事变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了解我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还要讲明如何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的。
我每天念《圣经》,《圣经》上也写着,上帝将派一位女人来救我。果不其然,夫人冒险飞来西安……” “蒋先生,”陈布雷有点为难,“我没有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重望。”
其实,陈布雷从侍从室一些随从人员口述中已经知道得比较清楚。 “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的写好了。”
蒋介石道:“我相信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嗯!” 陈布雷勉为其难,开始动笔,但写了不久,陈布雷感到心中很烦,写不下去了。一方面是来客太多,蒋介石住在溪口后,看望、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他委实也编不下去了。
有一天蒋介石把他叫去坟庄,问:“布雷先生,你写得怎样了?” “这,这……蒋先生,溪口近来人太多,太热闹,我心静不下来。” “这倒也是,”蒋介石从床上半欠身子道:“这样吧,你到杭州去吧,到里西湖新新旅馆开一间房间,安安静静写吧!” 陈布雷于是到了杭州。
在新新旅馆的一间房间内,写字台上摊满了稿纸,有许多已团成一团。温文尔雅的陈布雷,一反常态,把狼毫笔在墨盒里乱戳,猛地戳断了一枝笔头,夫人王允默又递给他一枝,陈布雷蘸了蘸墨汁,在纸上又涂了起来,一会儿又把纸捏成一团,掷笔长叹一声。
站起身来,在房子内来回踱步,浓眉紧锁,脚步声也特别响。王允默婉言相劝,叫他慢慢写,可是陈布雷忽然大声说:“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 王允默有点害怕,连忙请了陈布雷的亲妹子来,说:“你哥哥这次不知怎么的,火气大极了。
我讲几句,他大喊大叫。你的话,他还比较肯听。”
可是胞妹这次也不中用。她说:“二哥,你坐下来,喝口茶,心静下来,或者去西湖边散散心。”
妹妹的口气很温和。 “出去!你们统统出去!”一向性情温厚的陈布雷简直变了一个样,暴躁、粗鲁。
“二哥,千万息怒,这样动肝火,要伤身体的。” “唉!你们懂什么,”陈布雷拿起笔,他愤愤地说:“叫我这样写,怎能不动肝火!”猛地在墨盒中一戳,又把一枝毛笔头折断了。
但是,最后陈布雷还是把《西安半月记》交了出去。 不过,他在日记中却写了这样一段话:“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
2.陈布雷国不分何地为蒋介石写的,抗日令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3.陈布雷国不分何地为蒋介石写的,抗日令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4.陈布雷
戴光中:陈布雷死因新探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于王气黯然的南京城。
半个世纪来, 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人生之谜,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众说纷纭。 最近,笔者蒙布雷哲嗣陈过先生厚爱,惠赐其父日记之影印件供我研 究,终于从中发现了他自杀的真实原因。
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因病魔缠身,早有引退之意,但是,个人经 济及家庭前途,却逼迫他欲罢不能。当时,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忙着 “五子登科”,可这位清廉自守的书生,竟在日记中发出如下悲叹: “与家人筹划此后生计,不仅无片椽尺地足以在外栖旅,且以币值降 落之故,亦略无余储足以坐食三个月。
年力渐衰,乃感如此严重之经 济压迫,询乎愚忠直道,难以行于今日之世也!”(1945年10月14日) 所以,在此后三年中,陈布雷始终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不从政则无 以维持家计,既从政则必受精神上之折磨而日衰日惫以致油尽灯枯。 然而即便如此,他对“党国”仍是忠贞不二、鞠躬尽瘁。
其日记称: 五日来精神颇感疲惫不支,客人散去时,只能偃息于沙发榻上, 不复能长时期久坐也。今日为四明董事会,余本欲赴沪出席,然恐京 中人手稀少,因是中止。
近日(吴)铁城、(吴)鼎昌等均赴锡、沪 游览休息,(孙)哲生亦赴沪,(陈)立夫将出国,彼等能学太上之 忘情,而余独不能,人嗤其愚,我自有其守也。 (1948年5月29日) 近日所见所闻,皆是一派悲观散漫之论调。
昔人所谓未可共患难 者,已显露其端倪,瞻望前途,实属不堪设想,余本为消极保守一型 之人物,数月以来,鉴于内外艰难,以为终须有少数忠贞不二之士, 坚定信心,竭诚贡献,故他人规避、牢骚,余均处以怡定。 (1948年 8月7日) 事实上,甚至在陈布雷的最后一篇日记(11月11日)中也没有打 算自杀的迹象:“傍晚,觉体力心力不支,不能不作短期二三天的休 息。
晚餐后作致友人函札数件,并整理物件,十一时寝。”那么,究 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陈布雷突然自杀的呢?答案就在他11月12日写的绝 笔《杂记》里面。
这篇《杂记》发表时,是不完整的,国民党为了掩 盖真相,卑鄙地擅自删去了两大段至关重要的文字。一段是开头部分: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我之身体精神,今年乃一衰至此。
许身于革命,许身于介公,将近二十年,虽亦勤劬,试问曾有一 件积极自效之举否?一无贡献,一无交代,思之愧愤,不可终日。 “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我之谓也。
狂郁忧思,不能自制,此决无一词可以自解者! 抛妻撇子,负国负家,极天下之至不仁,而我乃踏之,我真忍人 也。然我实不得已也。
时事已进入非常时期,而自验身心,较之二十六年秋间,不知衰 弱到多少倍。 如此强忍下去,亦必有一日发忧郁狂而蹈此结局也。
闻朋友中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如有人问我,我将 答之曰: 我惟有一死而已。
上述文字,发表时全被删去。另一段是在“想来想去,毫无出路, 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 身自处者”之后紧接着———“太不相应了!思之思之,为此繁忧已 二十天于兹,我今真成了‘忧郁狂’!忧郁狂是足以大大发生变态的! 我便为这种变态反常的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岂非天乎?” 这些被删的文字告诉我们,陈布雷所以自杀,是因为共事的党国 要人们,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不能精诚团结、患难与共,反生离异 之心,互询善后之策,而自己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致使刺激过度、心理变态,突发忧郁狂,决定为垂死的党国“从一而终”。
他的同事 们,则在羞愧之余,更怕影响士气、加速瓦解,乃昧着良心抹去这些 文字,反冠以“感激轻生以死报国”的名义,造成了五十年来未能破 解的人生之谜。 但是,正如前述,陈布雷直到11日都没起过自杀的念头,他这 “忧郁狂”何以会突然爆发呢?陈布雷身边的副官、秘书都怀疑是蒋 介石的刺激所致,其实不然。
陈布雷写日记的习惯,是早上起来记录 昨天经过。也就是说,直到12日早晨,他的心理还完全正常。
这天, 陈布雷未曾出门,来访的也只有陈方一人,促膝倾谈达两个小时。他 俩的关系,“情如手足,人生知己”,因此,可以断定,“朋侪中有 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的消息,正是陈方于当天所言,令陈 布雷无法不信。
而他又是个极其敏感、神经异常脆弱的人,一点儿小 事都会让他寝食不安,这消息无疑如五雷轰顶,再加上蒋介石心腹秘 书周宏涛的态度——“追忆昨日周宏涛兄来谈时之情绪,可以反映中 心领导之已发生动摇。”(11月3日)——这就足以使陈布雷突发“忧 郁狂”。
因为他是全心全意为党国服务的,“竭己尽命,不敢少休, 既捐弃嗜好,复摒绝游乐,虽日尽十余小时之工作,犹嫌力不从心”, 没想到结果却是“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怎能 不使他忧愤欲狂呢?一介书生,满怀爱国赤诚,不幸误入歧途,又囿 于传统理念,昧于民心向背,于是,何以解忧,唯有自尽! 陈布雷之死,诚如其夫人所言:“谓非时代之牺牲者,抑何可得?” 光明日报1999。
2。1 。